一针见效的“神针”,到今天已经被滥用30年
生活资讯
2024-07-17
新闻来源:hsh
提示:新闻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
新冠高峰才过去月余,近两周各地又迎来流感季。城市里,有发热门诊彻夜的长队、医院药房断货的奥司他韦,而农村和乡镇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度过。
在华东某村,卫生院并不是多数村民治感冒的首选,上罗大夫那儿打一针才是——罗大夫是村里的赤脚医生,“一针治感冒”,撑起了他的“神医”口碑。
村民陈丽琴也和大家一样信任罗大夫:“他连新冠都只要几针就能治好,而我过年在县医院治的新冠,拖足了两个星期。”
“我以前到乡卫生院问过能不能给打‘感冒针’,医生说不能,想打消炎药也要先做检查、抽血。”
可是在村里大多数人眼中,感冒发烧还要做检查,钱和时间都消耗不起。卫生院医生说的耐药性、毒副作用,他们大多一知半解,甚至将信将疑。生活要求他们尽快消除症状,省钱和好得快就是最核心的诉求。
同样的事,在许多不同的农村和乡镇都正在发生。从卫生院的候诊区,到诊所门口的一排排塑料椅,都坐满了等着打针的病人。没有谁期待测了抗原用什么药抗病毒、血检后决定要不要抗生素。
一针“感冒针”,是基层最主流、最有口碑的治疗方案。
新冠高峰后的流感季,“感冒针”还是主角
所谓“感冒针”,是“抗生素+抗病毒+解热镇痛+激素”的肌肉注射组合,不同医生组方会有些许不同。
首先,抗生素并不会先查血再决定如何选择,而会使用克林霉素、林可霉素、庆大霉素等相对广谱、便宜的种类,甚至联合使用。第二,抗病毒用药也不会通过症状经验性选择,更不会测抗原判断流感类型,而是使用广谱的利巴韦林。
第三,解热镇痛不使用布洛芬、乙酰氨基酚这些单一成分的药品,而用安痛定。安痛定本身就是一种复方药物,含有安替比林、氨基比林和巴比妥钠。
前两种为 NSAIDs,氨基比林半衰期长(12 小时)但起效慢,安替比林则半衰期短(1~4 小时)但起效快,两者配伍实现既速效、又长效。而第三种成分巴比妥纳,则既有镇静作用,又能协同解热镇痛。
而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兼具抗炎、免疫调节、抑制下丘脑对致热原的反应的作用,则加成了其他组分的效果。
似乎可以这么总结:所有和感冒症状相关的药,“感冒针”做到了一针打尽。
“感冒针”处方 图源:医生提供
华中某镇卫生院医生徐卫宁,今天看了三十几个病人,近一半处方用了“感冒针”。
“几乎都是病人自己要求,说就开上次的针。”
在刚刚过去的新冠高峰期,徐卫宁所在的卫生所病人骤增,在几天之内从每天三四十直奔两三百。很多老人发热三四天了才来,缺设备看不明白到底有没有肺炎,甚至因为患者太多,连查血都难以保证。
“在卫生院四年多,‘感冒针’早有耳闻,但我从不主动开。”徐卫宁说,“但当时缺人、缺药、缺检查设备,新冠特效的抗病毒药就不用说了,输液器都缺,布洛芬也只撑了两三天。到了什么都缺的时候,就顾不得了。”
发烧到 39℃ 以上的病人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,徐卫宁和同事尽量了解基础疾病情况,看看血象、胸片。而更多的病人会直接开“感冒针”。
“感冒针”通过肌肉注射给药,相比输液大大缩短了病人在院时间;没了头孢、克林,还可以用林可、庆大,药品就显得相对充足;用上安痛定和激素,病人一定能退烧、周身疼痛能快速缓解;足够“广谱“的用药,也减少了问诊、检查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。
在高峰中的那几个星期,徐卫宁在现实的挣扎中,还是接受“感冒针”的一项项“优点”。
图源:视觉中国
高峰过去后,徐卫宁不止一次反思过给病人打“感冒针”,是不是自己的科学意识开始滑坡。但被他形容为“兔子急了咬人”的应急措施,却收获了比往常多得多的肯定:“
一位大娘还夸我治新冠比平时治感冒强,年轻人也进步了、有两把刷子了。”
“他们(病人)只知道赞‘感冒针’好用、良心医生良心诊所,其实很多都不知道用的哪些药。”现在应急时期过去了,今年的流感季却让徐卫宁感觉到了空前的为难。
因为新冠时遗留的好印象,要求打“感冒针”的病人比原先多得多。对此,徐卫宁依然有自己的坚持:“新冠高峰是一时的,但感冒不是,我不会主动开‘感冒针’。”
“当然了,我的坚持不一定有多大用,到了诊所和赤脚医生那里,只会用得更多。”
其实就算是诊所的大夫,也并非不懂“感冒针”存在的规范性、安全性问题。“这个处方不必是呼吸科专家,很多医生看到都会觉得离谱。但所幸也没出过事,就一直用下来了。”华南某镇诊所医生郑昌林表示。
“虽然在用,但一般也不会和患者说明这针里都有哪些药。”
一边劝熟人不要打,一边每天开出十几针
“患者开玩笑说,诊所医生比我会治病。”
华北某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延聊起“感冒针”在基层的使用,觉得情有可原,又十分无奈:“这一大套药当然会见效,但显然既不规范又不安全。”
感冒一般分为“普通感冒”和“流行性感冒”,可能需要且有特异性抗病毒治疗药物的是流行性感冒,由甲、乙、丙三型流感病毒引起。而普通感冒病原体为鼻病毒、冠状病毒、副流感病毒等,一方面尚无特异性抗病毒药物,另一方面免疫系统在 3~5 天内就可以把病毒清除。
1972 年广谱抗病毒药利巴韦林问世,“病毒唑”这个俗称,让人以为它对什么病毒都管用。事实上,国食药监注 [2006] 69 号文件已写明:本品适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与支气管炎,皮肤疱疹病毒感染
[1]。
WHO 现行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提示:“利巴韦林用于治疗丙型肝炎和一些病毒性出血热的治疗。”
利巴韦林用药信息 图源:WHO 基本药物标准清单电子版
同时,在 WHO 药品不良反应数据库中,利巴韦林的不良反应报告共 96353 份(截至 2023 年 3 月 5 日),涉及不良反应 23 万余例次。早在 2006 年国家药监局已通报警惕利巴韦林的安全性问题,指出“应对其生殖毒性和溶血性贫血等安全性问题予以关注”[2]。
因此不论病因和症状,使用利巴韦林无差别治疗感冒,既不规范也不安全。
“感冒针”中必备的抗生素,更是存在根本性问题:抗生素只对细菌有效,对病毒引起的感冒并无效果。不加区分的给感冒患者用抗生素,对病情无益。
抗生素的诞生曾大大降低了许多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。这样的“神奇”作用让人们无比信赖抗生素,我国逐渐成为生产大国后,也使抗生素迅速普及。
2021 年,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 发布了中国二级和三级医院门诊抗生素处方合理性大型研究结果。研究纳入 28 个省级地区 139 家医院的 1.7 亿门诊数据。结果显示,近 1900 万张(10.9%)抗生素处方中,高达 51.4%(968 万张)不合理,能直接判定为合理的仅 15.3% [3]。
2 月 10 日,the Lancet 刚刚刊登了一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所撰文章,提示防控措施调整后,短时间内新冠患者的激增,让我国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很快回到疫情之前,甚至更加严峻
[4]。
图源:the Lancet
而在解热镇痛部分,国家药监局曾要求临床应用安痛定务必加强用药监护,建议仅限短期应用、加强血象监测以免因血液系统反应造成严重后果。而很显然在打“感冒针”的地方,多数不具备血象监测的条件
推荐新闻

浏览量 84

浏览量 263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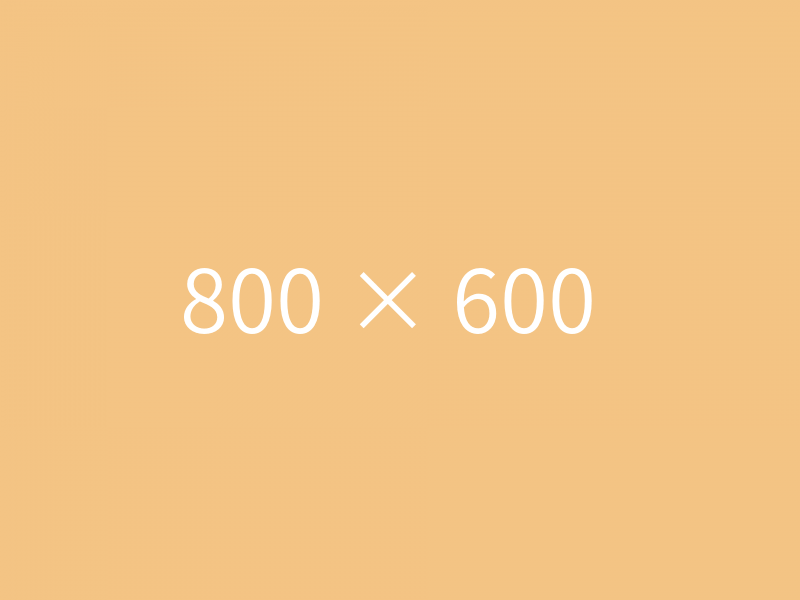
浏览量 38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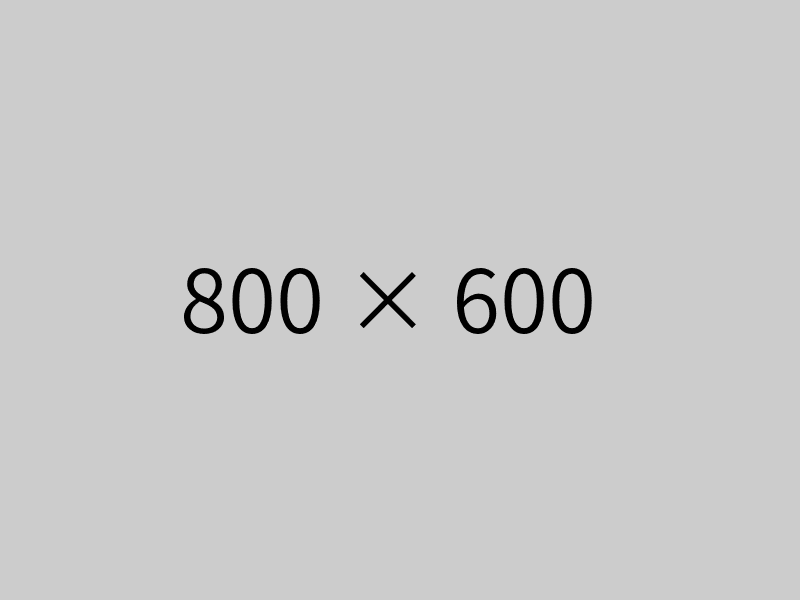
浏览量 8369




